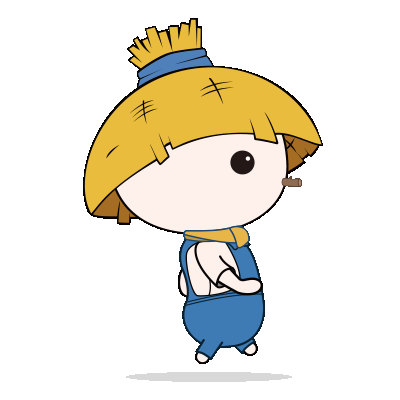祈思远被一个护卫拎着脚脖子来了一个倒栽葱,随着护卫的不断抖动,祈思远藏在身上的金条劈里啪啦掉在银砖地面上。
金银磕碰产生的声音听起来清脆悦耳。
但有人就不高兴了!
祈思远大喊:“我的金子,我的金子……”
他大头朝下伸手试图捞回地上的金条,被那个拎着他的护卫毫不留情的给带走了。
只有越来越渺小的声音传来。
少顷,连声音也听不见了。
乔鹤年低头整理袖口,状若无意的开口:
“听说,你前不久救了一个江洋大盗?!”真是胆子越来越肥。
时宜不甘的嘟囔:“谁这么嘴碎啊!这事也能传到你耳朵里去?”
陆深幸灾乐祸的火上浇油:
“啧啧!江洋大盗你都敢救,就不怕他反手扭断你脖子?小丫头人不大,胆子不小!”
这世上农夫与蛇的故事发生的还少吗?
时宜毫无形象的翻了个白眼,双臂抱与前胸,不服道:
“我是好惹的吗?一个重伤要死的人我还对付不了?看不起谁呢?”
陆深一摊手:“你看吧!我就说这小丫头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的。”
乔鹤年抬起他淡漠的眼皮,幽幽的看着时宜。
时宜顿感压力很大,用最霸道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:
“那我这么大的人了,好坏还是能分辨的,好吧!下次我改!我改。”
顶着乔鹤年冰冷的眼神,她的话越说声音越小,最后只得服软,口头答应改还不行嘛!
陆深饶有兴致的倚在金墙边上看戏,乔鹤年清冷的声音传来:
“知道你心软,但出门在外,保重自己最重要,别人的生死自有他的造化,你一个小丫头少掺和。”
时宜蔫头耷脑的答应:“是是是!我记住了。”
陆深摇头,这死丫头根本就是在敷衍人。
得!他们又都是瞎操心。
显然,乔鹤年也是知道这丫头的脾性的,靠她能改是不可能的。
乔鹤年:“江彣他们我已经帮你调教好了,现在就能为你所用了,今后你再出门让他们在暗中保护你吧。”
时宜眼神大亮,她也要拥有暗卫了吗?
陆深:“瞧她这没出息的样子!鹤年,你就纵容她吧!没有暗卫她都作天作地的,要是再给她暗卫,啧啧!她不得把天捅个窟窿啊!”
时宜不服气的蹦跶:“胡说,你少诬陷我。”
陆深两个眉毛炸起:“诬陷?呦呦呦!也不知道是谁呀?大闹某知府后宅,差点让人抓住给咔嚓了。”
时宜掐腰反驳:“那个知府都要老死了,一个棺材秧子还要祸害一个十六岁的姑娘,人家誓死不从,他就要烧死人家父母!
你说这样坏透了的老东西,你要是遇见了能选择视而不见?”
见过不要脸的,就没见过他这么不要脸的!
还知府呢!整个一人渣!
陆深也学着她的样子一只手掐腰,一只手指着这个祸害训斥道:
“那你就胆大包天的跑人家里去闹?难道你没听过——破家的县令,灭族的知府!你那是作死!”
时宜掐着腰跳脚喊道:“胡说!我那明明是替天行道!”
陆深被她气的鼻翼快速起伏,恨铁不成钢的对乔鹤年说:
“你看到了吧!这就是个胆子大到没边的闯祸头子,你还给她送人,你这就是助纣为虐!”
乔鹤年头疼的捏捏眉心,
“那个知府……也的确该死,多行不义必自毙!遇到丫头也是他的因果报应。”
时宜扬眉吐气的对陆深做鬼脸,陆深脱了鞋就要抽她。
乔鹤年又说:“不过,时宜你的初心虽然是好的,但做法我却并不赞同!不管怎样,都不该将你自己陷于危险之中。”
陆深:“就是说啊,要不是我们当时有人在那里接应,小丫头,你就要被人家抓去给你最看不上的棺材秧子殉葬了!”
乔鹤年:“没错!时宜,你千万不要小看一个人的恶!那个知府一家子都是黑心肠!你还小,不懂这世间险恶到底有多恶心。”
陆深嫌弃道:“就是说啊,翅膀还没长硬,就老实的藏起来猥琐发育!等你强大到可以一根手指捏死他的时候,再出手!岂不是很爽!”
时宜深感无力:“那个老混蛋都已经要老的掉渣了,要是再晚点出手,我怕那姑娘就被祸害了。
而那个老东西到时候已经老死了,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嘛!有仇现场就报才最爽嘛!”
乔鹤年:“时宜,这世间不平之事比比皆是,你又能管多少?”根本就管不过来的好吗!
时宜无奈道:“起码看到的得管吧!”看到对面两人都露出不赞同的神色,她说:
“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,其实我也知道错了,我应该布置好再动手的,起码也要给自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