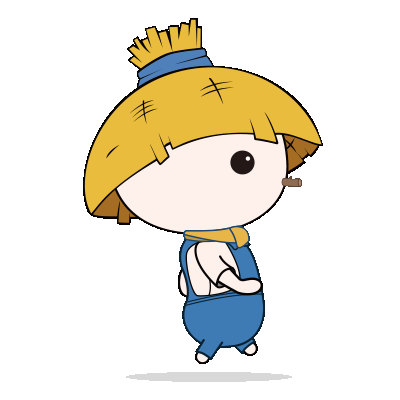“狄黛米。”他说。
“狄黛米死了多久了?”我看着阿罗的眼睛问:“一千年?两千年?为什么她的死让你无法释怀?真奇怪,你对于权力有这样浓烈的欲望,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,却因一个在两千多年前死去的妹妹而日夜痛苦吗?我猜你根本不记得她的长相了――你为什么要说谎?”
阿罗的表情迅速地阴沉了下去,他温柔可亲的躯壳在眨眼间就四分五裂了。我已经隐约触摸到了这个秘密的外壳:能赋予吸血鬼以永恒痛苦的只有爱人的死亡。我知道阿罗在隐藏这种痛苦,我只是不懂为什么。如果他的爱人已经死去,那么苏尔庇西娅是谁?这个秘密究竟还有谁知道?
“恐怕这就不属于你应该知道的领域了,费伊。”阿罗低下头看着我,睫毛将他的两只眼睛都笼罩在狭长的阴影里。我看不清他的神色,只能听见他一字一句,近乎威胁地说:“有时候不听劝告和一意孤行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你无法想象的。”
“那么杀了我吧。”我回答。“我欢迎死亡。”
在来到这里以后,我已经很少回想起以前的事情了――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事情。那时候我孤僻、固执、和任何人都难以成为朋友,有时候连续几天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,或者一连几个小时盯着窗外发呆。在认识我的人当中,善良的那一部分宣称我“有艺术家的气质”,而其他人则用神经病来形容我。我并不认为他们是错的,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没有明显的界限。当过度沉浸在戏剧与文学的世界中时,有时我会无法区分现实与梦境,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,这种情况愈演愈烈――直到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。文学作品是一种现实还是一种梦境,一种真实还是一种虚假?我们如何证明我们正身处真实之中?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笃定地确信唯有我们所处之地是真实,而其他空间皆为虚假?是谁教会我们这些的?
死亡与爱情,两个永恒的命题,从古至今已经被无数文学家和艺术家辩论过。人们通常认为爱情只不过是为人生锦上添花的装饰品,如同姜饼上的果仁;他们为书籍中所描绘的伟大的、疯狂的爱情落泪,却也永远将它们视为虚幻。而对我而言,虚幻即是现实。我钟爱虚幻。
一切生命都将终结,然而爱情永垂不朽;当爱情被毁灭时,我也将随之坠落。
“如果死亡能让我得到我想要的,”我重复道,“那么我欢迎死亡。”
“你以为你拥有这种权利吗?”阿罗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脖颈,他的手指冰冷,几乎像是一只吐信的毒蛇在舔舐我的喉咙。然后他悄无声息地消失了,沉重的疲惫感没过我的头顶,终于完全将我淹没。
我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在谈话后变得更好,恰恰相反,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,很少吃饭,开始过度依赖疼痛――摧毁性的疼痛,它让我觉得我还活着,只有疼痛能让我麻木的大脑重新运转。我在每个寂静的清晨来临时站在镜子前,神经质地撕扯自己的头发,用纤薄的修眉刀割破掌心,然后看着鲜红的血液从破损的皮肤里流淌出来。对我来说,这是一把病态而有效的,用来唤醒我的一天的钥匙。每一次伸出手去抓握什么东西时,伤口会再次开裂,我从这无数次的折磨中获得怪异的快感。
我开始用更长的时间来发呆,不思考任何事。在任何布满灰尘的角落,阴冷、潮湿的房间,没有火把的空旷走廊里,我躺在地上,把整座城堡幻想成一个棺材。我在这里永久地、没有期限地睡下去,直到我变成一具骨架、一捧灰尘,变成书架上一张语焉不详的羊皮纸,变成整夜燃着的火把,变成空气,变成任何东西。
我不清楚这样的日子究竟过了多久――时间已经变成无关紧要的因素了,当一切对于外界的认知都在退化时,你就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或太慢了。总而言之,在我不知道确切日期的某一天,我再一次见到了阿罗。
他站在门口,外面的光亮从门缝间渗透进来,驱散了房间里浓郁的黑暗。我眯起眼睛看向那张熟悉的面孔,它的每一根线条都如此完美,过去我经常在日记里穷尽溢美之词来描写这种完美。我曾将它喻为最华美的钻石,但人造的珠宝却太过矫揉造作;后来我称赞它胜过达芙妮化身而成的月桂树,但植物只不过是充满杂质的寄生物;我还曾用黑夜,用繁星,用诗歌和音乐来描述它,却始终为它们的庸俗而苦恼。
这一刻我终于找到了远胜那些令我不甚满意的词汇的形容:这是一张怎样的面孔?我无法形容它,正如我无法形容爱情。它绝望而漠然,残忍而宏大,温柔而暴戾;它是这世上一切矛盾的集合体,一切美德与恶习的总称;它是无法拯救的罪恶,无法原谅的错误;它是真实的虚假,虚假的真实。它是我的爱情。
“你究竟想要什么呢,费伊?”阿罗轻声问我。
“真相。”我用颤抖的、嘶哑的声音说:“纯粹的、简单的真相。”
“真相,”他重复着,“真相鲜少纯粹,也绝不简单。”
“我不需要你朗诵王尔德的戏剧台词。”我生硬地打断他,然后阿罗沉默了。不知为何,我突然觉得我想知道的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