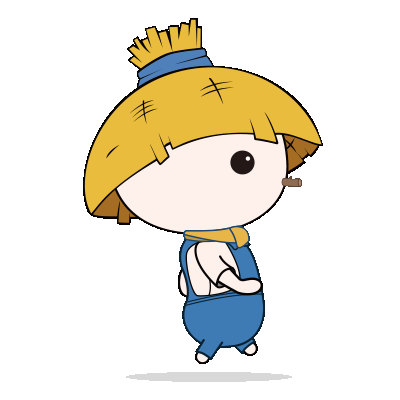,披头散发,流血不止,铠甲残破,马哀嘶鸣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冲到殿前。
“北……北军急报。”信者说完便倒地。
“快快,速传军医。”慕容霸急切的上前扶起信使,速唤左右军士,让这信使回营歇息。
慕容霸速拿军报呈于燕王。
“唉,北军俱危。”燕王猛拍一下大腿,掩其头,不住的叹息。
慕容翰拿过军报,看过沉默不语,将此报递于慕容霸及众将。出列向前,向燕王说道:“王寓此举,报有必死之决心,全军向北,背水列阵,为我南军赢得时间,但不成想王武听闻都城陷落,全军死战,更兼得已破近扶余之境。扶余王素于我有隙,虽臣服于我,然见此败军,撤河上浮桥,紧闭城门。”
慕容翰跪下,悲痛道:“可怜我燕国将士,要被这高句丽王其弟,王武逼入死地,高句丽断无可恕。”慕容翰紧握其手中金刀,像似要折断。
“儿臣愿往,誓报此仇。”慕容霸上前,“我愿率军直攻高句丽王武偏师。”
燕王正欲传令,韩寿进言道:“大王,主不可以怒而兴师,将不可以愠而致战,合于利而动,不合于利而止。”韩寿直接往朝堂中央一站,说道,“如今高句丽丸都城已破,敌人已是逃散。如今北军大败已是板上钉钉之事,若仓促进军,可能胜而转败,望我王三思。”
那慕容皝,慕容翰到底是久经战阵之人,暴怒之心渐渐平息。却见慕容霸,颇为愤恨,向燕王道:“儿臣愿带本部人马前去救援,不劳动大军。”
“你且给我站住!”燕王怒道,“没有孤令,你不可擅动。”燕王嘴唇都抖动了。
“父王,北军危矣。”慕容霸还欲进言。
“左右,把慕容霸给我拿下。”燕王不由分说,过了许久才缓缓坐上王座。
韩寿继续进言道:“为今之计,当速收敛众军,命各部追击将士速归本营。合兵一处方能妥当。”
燕王赞许道:“韩长史思虑周翔,先王曾对孤曰:‘吾幸得寿而入棘城’今孤得寿言,方取这高句丽之地。”
韩寿拜道:“燕王过誉,下臣不胜惶恐。”
燕王想定,传召:“召慕與泥速回丸都,其余各将尽数归位。”那慕與泥的信使得令速速赶回。
“却有一事,孤想问计于你。”燕王想了一会儿,向韩寿问道,“如今看来北军将败,高句丽此地不可戍守,我恐大军将去,复为高句丽所占,岂不白费我众将士心血,孤欲奈何?”
韩寿略微思索一番,“高句丽之地,诚然不可戍守矣。今其主亡民散,潜伏山谷,大军既去,必复鸠聚,收其馀烬,犹足为患。”
慕容翰问道:“我大军驻守也不在话下,下臣原意以身犯险,为我燕国镇守这高句丽。”
燕王沉思,说道:“翰兄此举壮哉,但如今国事纷杂,猝然镇守一隅恐于大军不利,且听听韩长史有何谋划。”
韩寿眉头紧缩,眼睛阴沉,说道:“行军打仗,我不如将军,阴损毒辣之事将军不如我。”
“此话怎讲?”燕王好奇问道。
“请载其父尸、囚其生母而归,俟其束身自归,然后返之,抚以恩信,策之上也。”韩寿只冷冷的回答道。
“毁人父尸,于常理是为不妥。然如今乱世,纲常礼法合则用,不合则弃,且高句丽本为化外蛮夷,不用那么顾及。”堂下鲜于亮回道,其人虽为赵国降将,但鲜于本为匈奴姓氏,未沾多少王化。
“燕王,我燕国大军素以解民倒悬,惩恶扬善著称,今毁城戮尸,恐有大患。”慕容翰上前跪下,说道。
“王兄此意,尽为妇人之仁。今我大军孤悬高句丽,且其北路未平,我燕国将士连年征战,血流尽了。若不永绝后患,我妄为燕主”慕容皝发怒,“传我军令。”燕王起身,“掘王钊父乙弗利墓,载其父尸。”顿了一下再道,“收其府库累世之宝,尽虏男女人口,烧其宫室,毁其都城。众将士,在孤之后,没有丸都城!”
韩寿向前,只更为恭敬言道:“燕王此举,诚然是也。石赵意欲图谋我国,高句丽与其素有勾连。先前赵国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,夹攻我燕国。前岁襄平之围,辽东之危,慕容仁叛乱,高句丽皆为祸首。背燕者如佟寿、郭充之流尚在高句丽。今破都毁城,掘墓鞭尸,定令其胆寒,忧惧。”转身向慕容翰拱手道,“将军宅心仁厚,无可指摘。今我大军已破其都,且高句丽所依仗者,唯丸都城一城尔,若尽废其城,此戎狄无所据矣,必束手而降。”
燕王称善。
众将皆领命。
“王伯,王伯,你且起来,霸儿扶你。”这慕容翰跪了许久,待众将都散去后,慕容霸上来了,扶着王伯起身,退回军营中。
南路大军终于撤出了丸都城,留下了是一座烧焦的,伤透了的废城。四周断壁残垣,残破不堪,城墙坍塌,碎石断砖,那高句丽王的宫室印在了一片熊熊火光之中,全城已无一处完整的居所。高句丽的府库全数被洗空,累世积累的财宝如今已当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