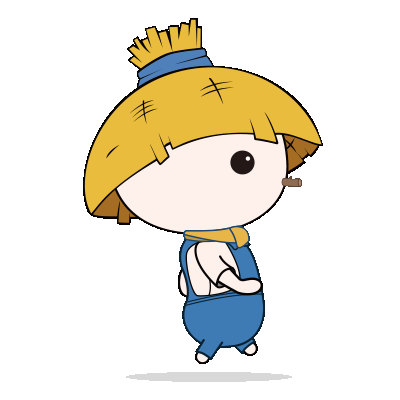在床上躺了两天的虞杳,终于理清了脑子里的那团乱麻;
梦中那个站在悬崖边上,一身死寂、或者在大火中不断挣扎、或在血流成河的死人堆中哀哭断肠,并苦苦哀求她活下去的女子,是和她同姓同名不同字的——虞窈,小名桃桃,因出生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得此小名。
虞窈,乃元启朝.神武将军虞靖飞之长子——虞驰正的嫡幼女,也是虞家两代唯一的女孩,受宠程度自然不用多说,凭其小名便可窥得一二。
眼下正直二月末,虞窈因身体不适,便未随母亲和兄长,以及祖母婶娘这些神武将军府家眷一起进京,而是留在凉城,打算跟着祖父,父亲,以及虞家军同行。
谁知,短短几日后,虞窈不但病情没有一点好转,竟毫无征兆的发起高烧,整个人差点儿被烧糊,让其祖父神武将军,和其父镇军大将军好一通担心。
这不,一场无厘头的高烧把虞窈烧成了虞杳,脑子里还多了些诡异莫测的记忆;
或者说是虞窈的亲身经历吧!
经过两天时间的梳理,虞杳把这些记忆归为虞窈前世的遭遇。
至于她为何突然来到这个世界,大概也和虞窈脱不了关系吧!
只是如今说什么都晚了,虞杳只好默认,并无奈接受眼下的一切。
好在脑子里有虞窈的记忆,倒也不怕穿帮。
至于那些杀戮,以及虞窈的悲惨经历,虞杳也并未忽视,而且非常认真的梳理一遍;
得出的结论便是虞家兵权在握,势头无两,引起狗皇帝的猜疑,于是下旨让虞窈嫁给太子。
小姑娘大婚后,不但丝毫没有改变局势,到最后眼睁睁看着虞家满门被斩,看着亲人的尸首悲痛哭喊……
画面断断续续,但凭借着这些残存片段,虞杳理出了这么子个故事线。
至于梦中的那场大火,看周围的高阁楼台,估计是在宫中!
而最后虞窈一身死寂站在悬崖边,回头哀求虞杳照顾好她的家人,不用想也能知道小姑娘最后的结局!
不得不说,这确确实实是一场来自皇权的杀戮,是一场英雄的悲哀陨落。
“飞鸟尽,良弓藏,狡兔死,走狗烹!”
看着眼前的棋盘,虞杳低吟,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悲凉。
她盯着棋盘上的黑子和白子认真思索一会儿,便把一颗白子后退,瞬间,整个棋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退既是进,慢即是快!”
说着,她放下手中的棋子,居高临下纵观整个棋局。
“既然无法改变世道,那就改变自己。”
说着她纤指一夹,一颗白子完全跳出棋局,成了一个旁观者。
“不够!”
“袖手旁观有什么意思,做执棋者才有趣!”
“哗啦……”
话毕盘翻,油润饱满的黑白棋子撒落一地,响声也惊动了外面的丫鬟。
“小姐,可有伤着?”
春柳疾步进来,一脸担忧紧张问虞杳。
看着春柳,虞杳眉头轻皱一下,而后面不改色冷冷吩咐;
“收拾了!”
“是——”
不知怎么的,春柳总觉得小姐看她的眼神儿格外奇怪,说不上讨厌,但也没有往日的喜色,她疑惑满心,战战兢兢蹲在地上收拾棋子,一边仔细回想最近有没有做错什么……
直到洒落一地的棋子全部收拾完,春柳也没想出个所以然,只以为是她家小姐大病初愈心情不佳所致,随即便悄悄退下,不敢发出任何响动。
出了房门,春柳才长喘一口气,并轻拍几下胸口。
“这是怎的了?”
突然,冬麦不知从哪窜出来凑过去问,吓的心神不宁的春柳一大跳。
“死丫头,想吓死我不成?”
春柳拧着眉低骂着,伸手就在冬麦胳膊上狠狠掐了一把,直掐的冬麦呲牙咧嘴。
“谁惹着你了,竟拿我撒气!”
冬麦不服气,边揉胳膊边抱怨。
“莫要胡说!”
春柳边走着边回头看了眼主屋,又瞪了眼冬麦。
“你有没有觉着,小姐与以往不大一样了?”
俩人来到侧屋廊下,春柳盯着主屋门口小声问冬麦。
“小姐还是小姐,有甚不一样的?”
冬麦边揉胳膊,边不以为然的翻翻白眼回道。
“死丫头,哪有那样疼!”
“不过,我总觉得小姐大病一场后和以前不大一样了!”
春柳嗲骂了冬麦一声后,便又皱着眉头低声说。
“小姐病得那样重,人差点都没了,能和以前一样么?”
冬麦依旧不把春柳的话当回事儿,总觉得她在胡说八道。
“你这死丫头没心肝,你就没发现小姐的眼神么,看一眼我后背直冒冷汗,就像……”
“就像被什么盯上一样,手脚都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