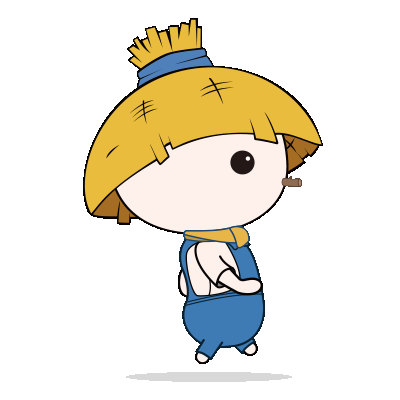“您……二位,可是娄良镇人氏?”
看清隔壁的两位老人,尤其是那位老者的长相后,虞杳便主动开口笑问。
那位清瘦虚弱的老者,正是娄商的父亲——娄四海!
身体的病痛,加上心里的煎熬,让娄父心力憔悴,面色如土,却还是警惕的盯着虞杳仔细打量,思虑再三后,还是选择如实告知;
“正是!这位小公子,听着好像是外地来的?”
娄父与娄商五分像的长相,让虞杳态度格外客气,并笑着回话;
“没错!您老好耳力!”
虞杳的夸赞让连日忧心的娄父挤出一丝笑容,看了眼身旁沉睡的老妻,他小心挪了挪身子,靠墙看着虞杳又问;
“不知,小公子打哪儿来?”
“小子打西边儿来!”
闻言,娄父明显一愣,再次盯着虞杳一番仔细打量后,便激动挪上前,双手抓着牢房的栏杆,颤抖着声音低声问;
“可是……六公子?”
虞杳立即起身,紧紧握住娄父的双手低声回;
“正是小子,让伯父遭罪了!”
娄父却激动的连连颤抖,喉咙发出‘呼噜’声,他却强忍着没咳嗽,而是满含愧疚,双眼湿润的低声道;
“你……终究是牵连你了,让你也淌进了这潭祸水!”
虞杳警惕的看了看外面,见门口的压抑正睡的鼾声四起,便压低声音问;
“伯父,到底出了何事?”
娄父也看了看外面,就同虞杳道;
“此事……唉!”
一声叹气后,娄父一脸悔恨的靠着栏杆坐下,接着就娓娓道来;
“都是老夫有眼无珠,信错了那娄江小儿,才给家里招来了这般祸端……”
娄江?
“可是您府上的管家?那娄海的兄弟?”
娄父大惊失色,盯着虞杳就问;
“你怎么会知他们兄弟二人?难道……”
说着,娄父不安盯着虞杳;
“你遇到他们二人了?”
“小子遇到了那娄海,便向他打听了你们的事,不想……”
“无耻之徒,是老夫有眼无珠,错将饿狼当良犬养了多年,到头来却害的家破……”
“伯父,还没到那一步,你先告诉我,敬诚兄他人在何处?”
闻言,娄父连忙擦了擦眼泪,这次看了一眼外面,便小声对虞杳说;
“我儿娄商,他被都司——漕袁山给带走了!”
说起儿子,娄父又是一阵揪心不安,甚至不敢想,他到底是死是活!
虞杳怎么都想不明白,漕袁山为何要带走娄商?
按理说,两人应该没有什么交集!
“到底因何原由?”
“粮!财!”
娄父咬着牙吐出这两个字,且满眼恨意!
至此,虞杳终于猜到点什么,却也迷糊不清!
漕袁山身为上岁都司,这么明目张胆的行事,到底为什么?
“既然他朝粮和钱财而来,为何要将你们关入大牢?”
“因为……”
说着,娄父露出一脸忌惮,却在虞杳的注视下又压低声音道;
“他私底下与鄱芜勾结,被我儿撞见,所以他想……杀人灭口!”
瞬间,虞杳倒吸一口凉气,甚至都不敢想象后果!
立即抓住娄父的手腕追问;
“伯父,此话当真?”
“我儿被抓之前,亲口与老夫说的,又怎会作假?”
说着,娄父又叹了叹气道;
“都说神武侯治军严明,如今看来……”
娄父讥讽一笑,低头不再言语,虞杳的内心却如同压着一座石山,让她喘不过气来!
这事儿也能牵扯到神武侯?
确实有关系!
毕竟,如今是他掌管南川,漕袁山也算是他的手下!
但是虞杳不能容忍这等卑鄙小人,污蔑祖父的威名,便格外严肃道;
“娄伯父,漕袁山的所作所为,与神武侯没有丝毫关系,这点,请您放心!”
娄父一脸吃惊,盯着虞杳讷讷道;
“你……”
“小子会向你证明一切!”
说完,虞杳坐回去,想着如何将娄父娄母一起带离这里!
闭着眼睛想了半天,突然,虞杳睁开双眼,起身踹着牢房大喊起来;
“来人,死哪去了!”
“谁在见?大清早嚷嚷什么?”
被吵醒的衙役,怒气冲冲呵斥着来到虞杳牢房外,挥舞着手中的棍子就要打人;
却听虞杳嚣张至极的命令道;
“去,让漕袁山来见本公子!”
衙役一愣,赶紧揉了揉眼睛,确定自己没有做梦后,便一脸不屑的冷哼;
“年纪不大,口气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