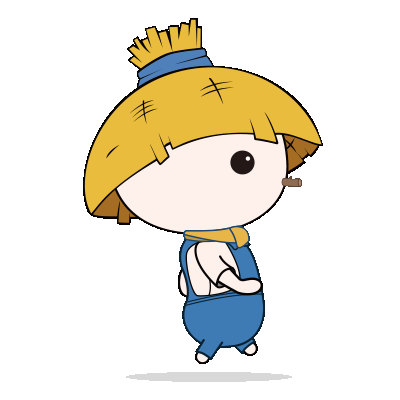“母亲最近在宫里可好?”贺兰修宜如常的坐到太后对面,为自己倒了杯,并没有喝,只是拿在手里轻轻的打着转。
杯中晃动的茶水,尤如她此刻的心情,难以平静。
对于眼前的母亲,她不知道该用何种态度去对待。
无论当初她抱走自己时是何种心态,可她对自己是发自真心的宠爱与保护,自小她身上的衣服,一针一线皆是出息于她的手。好几次她遇袭,都是她身边的暗卫出手相救,就是那次差点儿要了她命的大火,续命之药也是她丢下了脸面去求来的。
可她害了自己的生母,这也是事实。
按理,她该为生母报仇。
按情,一百二十几年的养育之恩,她不能不报。
“你为何,不对我狠一点。”起码这样,她能报仇报得心安理得。
“什么?”太后放下茶杯不解的望着她,贺兰修宜的声音太小,她并没有听到她说了什么。
“没什么,听说最近父亲最近又纳了几个妃子,母亲可有受到欺负?”勉强了自己,同时也是苦了自己。
贺兰修宜与往常无二的与太后闲谈起来,可又有谁知,此刻她的心中,那寸寸已经裂开的伤痕。
“也就如是,哪年不是新人进旧人出?你父亲的性子你应该知道,他若是不如此,那便已不是他了。至于母亲,你不必担心,那些小丫头还入不了母亲的眼,再说了,母亲已是太后,她们也不敢如何,毕竟太上皇只是太上皇。”
身为皇上的女人才有得争,为自己而争为未来或已有的孩子而争。太上皇的女人,已经没有太多争的必要了,佐不过是附于男人而生的可怜虫而以,不足为惧。
“不扰母亲就好。”
太后慈爱的看着贺兰修宜:“你不必担心母亲,母亲有你如此优秀的女儿,谁敢给母亲脸色看?”眼前的女儿,是她这一生的骄傲。
贺兰修宜想像往常一样的笑,可扯了几次都没有扯动嘴角。
太后已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,并没有发现贺兰修宜的异常,嘴角上扬的幅度说明她此刻心中所思是值得她开心的事情。
“哦,对了,这次的兽潮,我听你父亲说是由你领队?”这是她今天特意路过的原因,去庙中祈福,也是为她女儿而祈。
贺兰修宜点头:“我现在身体已然大好,即是占着国师之位,就要做其位之事。”
北辰四面环山,兽潮来临时是一年中最为危险一刻。几乎年年都要求助于其它大国,可哪个国家兽潮来临时不要抵御?
但今年不同,北辰派去焱昱相商的使臣带来了好消息,其它几国都会派人前来帮助。
所以名为她来领队,说到底还是各司其职,左不过是她要付出的精力要多些,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,那两父子抱着何种心思,现在的她又岂能不明白?
一切顺利,身为国师的她,自是应当。
若有不顺,那一切的责任都在她身上,甚至。。。她已不配这一身国师之服。
“修宜,此次你不可接。”太后太过了解那俩父子,都是一向的自私一样的无情,已经一次次的算计修宜,现在修宜已然大好,他们怎么可能会放过兽潮这样好的机会?
搞不好有着大阴谋等于修宜。
“母亲,我身为国师,为国为民是应当之事,抵御兽潮之事,就是他们不提出来,我也得前往,左不过一个是不是领队的问题。”悠闲的为自己倒了杯,贺兰修宜像是没事人一样朝着太后举杯雅饮。
“可你明知。。。”
“嘘,母亲,有些事,不可说。”贺兰修宜纤细的手指轻压唇间,朝着太后淡淡一笑。
太后:“。。。。。。”
罢了,罢了,她已经老了,有些纷争相斗,已不是她这个快要入土之人可再操心。
“你即要前往品城,那母亲也不再闹你。不必送了,就几步路,母亲认得。”太后定盯眷恋的看了眼贺兰修宜,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。
贺兰修宜动都未动一下,手中杯,杯中水一晃未晃,如此静坐在窗侧就是一下午,迟来的夕阳下,将她的背影越拉越长,空留下寂渺一室。
却是不知,太后出了国师府后,停下了脚步又再次转头,望着如幕在竹林中的国师府,两道清泪缓缓滑下。
‘视你第一眼,母亲的人生已然圆满,如何还能再对你狠心?修宜,此生,母亲知足了。母亲等不到你回来了,但望着,在母亲的陵前,你能不再恨母亲。’
她哪是没有听到,她是不敢听到。
‘修宜,原谅母亲的自私,母亲只是想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刻,还能听到你叫我为母亲,而不是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母亲。’
一声轻叹随风而去,不知叹的是谁的人生。
“爷,北辰国师求见。”乡间小屋前,夜九禀报。
“请她进来。”
“是,国师请。”
门帘轻启,一身标志北辰国师服的贺兰修宜走了进